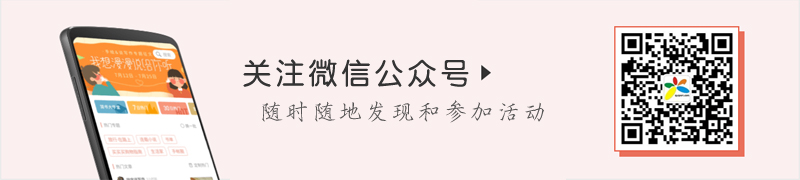隐秘的桃花源
一坐车从墨脱到背崩乡只是二十多公里,但需要两个多小时。墨脱的路,有一小时10公里之说。这条路很颠簸,有很多急转弯,往下望去,就是雅鲁藏布江。这条路的危险性,会让城市里的司机毛骨悚然。我的视线被美丽的山水,云雾,峡谷,雅鲁藏布江所充分占据,而忽略了道路里暗藏的危机四伏。
这条路的开始,通往雅鲁藏布江的幽深,复杂的内部深处。一览不尽的青山绿水,马远夏圭的长幅横披。空中薄雾冥冥,是雅鲁藏布江发髻上的小花。江水是这里缔造者,背崩乡的村民,都是栖息在雅鲁藏布江的身旁。一排排木房子,沿山而建。全是两层的木质结构的房子,底下养畜生,楼上住人。我们越来越对经验之外的生活持着怀疑目光。在这里,你看不到刚劲水泥,看不到高楼大厦。市场,汽车,高架桥,超市,在这里没有赢得豁免权。我越来越感觉自己越走越远,从现代化工业城市,走到一个长期封闭的原始农耕社会,空间地域在连日来不断的转换,而转换的何止是空间,还有那看不见的时间。历史的痕迹,顺从着空间的拉出来的线索,渐渐浮出水面。当社会按照“进化论”的规律不断的向前进,当城市人们的脚步按照顺时针的方向急步行进。而我却在不停的后退,我所遵循的时间法则似乎与别人的有所不同,我的双脚似乎在城市里找不到落脚方向,只有在乡村小道才能找到容身之所。因此当每个人都往城市跑,而我却选择一种逆向行走。他们朝向的终点是死亡,而我走向的却是前世。
第一次来到这样的地方,感觉很熟悉,仿佛前世就在这里生活过,呼吸过这里的空气。可又觉得是那么的陌生,当一些门巴族的孩子,头上顶着一袋几十斤的粮食走过我的视线,我的内心一阵酸。他们的目光是那么的渺茫,带着几分的向往和疑惑。一路走来,还是看见很多背负重物的孩子,年纪轻轻,就被贫穷的无奈压垮了小小的肩膀。有些孩子,没有去上学。尽管现在九年义务教育,但有些家庭实在一无长物,他们靠一亩地,一些粮食来自供自给,一个劳动力的价值比送去读书换来的价值来得更实在些。于是,有些孩子因家庭原因被迫辍学,从小就开始走向背夫的生活。尽管现在通车,但汽车有钱人的产物。这里最通常见的运输工具是大卡车,而最直接的则是人体劳动力。这里的人,世世代代生活在与世隔绝的荒蛮岁月里,背夫不是一种职业,而是普通家里都应有的劳动力。五六岁的小孩便开始走向背夫的生活,双脚一辈子走过的路,任何精准的仪器都无法丈量出具体数字。我曾问过班里面的孩子,你们走路出过墨脱县城么?他们都纷纷告诉我,已经无数次了。他们与城市里的孩子不同,当城市里的孩子享受着麦当劳,肯德基,畅游网络,打着电动游戏机时,这里的孩子已经早早离开了家,肩上背上稻谷,粮食,货物,从起点走到终点,于是生命被放置险滩,泥石流,塌方之中。雅鲁藏布江赐予他们的原始的神巫文化,而道路的艰险,生命稍纵即逝,命途潜伏着诸多危险和不安,练就门巴族人强劲的筋骨,焕发了生命巨大的拼搏激情。这是充满苦难的民族,在百年来悟出的生命哲学。从孩子到大人,你可以从他们的默默低头做事,到露出笑容的那刻,看到历史赋予门巴族的人精神内核。
来背崩前,墨脱中学的校长说,背崩完整的保留了传统的门巴族特色民风,在那里我能到真正门巴族家做客,并喝到自家酿的黄酒。初到背崩,仁青校长便带我去当地门巴族做客。当地人有个习惯,有客至家,必得倒黄酒。黄酒是自家酿的,且现酿现喝,用手工做的铝瓢(门巴语称之为“酌”)来盛酒。铝瓢有各种各样不同大小的,但一瓢足足有好几碗酒。我喝一口,放下,主人斟满。喝一口,放下,主人又斟满。这样的动作不断的重复。在此过程中,主人一直站在你的面前,为你斟酒,直到把铝瓢的酒全部斟满为止。若你没喝完,主人就一直站在你面前,须臾不离半步,保持着斟酒的姿势,随时给你的碗添满。以致我一口气喝下了几大碗,也就是一瓢。这酒的度数不高,是用玉米和鸡爪谷酿就的酒。在六年级学生的文章里,我看到原来门巴族的黄酒是这样酿成的:先把玉米晒干,磨成碎,然后生火,把玉米烧熟。然后在另一个大锅里,放水,倒下刚炒熟的玉米,和鸡爪谷。煮熟后将它放在簸箕上,直到放凉为止。用米糖洒一层,用树叶盖上,过了几天收在塑料桶里,用盖子紧紧的盖住,收藏一个月就可以喝了。(尼玛央宗,格桑玉珍)
这些繁复的工序,在我喝的时候,是看不见的。我只看见几个长长的竹筒,吊在空中,竹筒里装满了玉米和鸡爪谷,主人需要隔一段时间往竹筒加清水。竹筒底有一小孔,会滴出黄色的酒来。于是,门巴族的黄酒是现酿现喝。主人一边在酿酒,客人一边在喝酒。酒是新鲜的,一滴滴的流淌下来,不缓也不急。带着主人掩不住的喜悦,暖入肝肠。我用刚学的门巴语“巴扎”(谢谢的意思)向主人道谢,主人一脸高兴,又盛了一瓢酒,倒在我的碗里。在门巴族做客,他们通常会将家里的最好的食物,最好的酒拿出来待客,这样的热情,慷慨,让人感觉到自己在享受着最高的待遇,并常有一种盛情难却之情。背崩的门巴族保持着百年来的文化传统。“每一个细节都体现了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,而做出天衣无缝的应对。”或许由于地域的偏远性,以及交通阻塞,长期的封闭性得以让背崩乡,在沧桑巨变中保持着一个前进世界里失传的桃花源。传统的生活方式,审美方式,以及待客之道,在长远的时间长河里依旧生机勃勃。这里的民风纯朴,从小孩到老人,说话的声音,呼出的气体都是干净的,没有丝毫杂质。如同李敬泽所说“村庄在乡土中国的灿烂星空里做着自己的梦,它们在呼吸,在执着地编织和传递着特殊的遗传密码。”
从门巴族的家里出来,我终于得知为什么自己的脚步总是处于奔波的状态。山中岁月,凝固了时间的流动。在越接近自然的地方,人也更容易接近内心灵魂。而在我所居住的城市里,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淡漠。一栋高楼大厦,聚集的人口甚至比这里其中一个村的人还要多,但人与人之间的交集却是恰恰成反比。除了觉得曾在电梯里偶遇过,这张脸孔很熟悉之外,你对此一无所知,谁也没有开口说过一句话。我们很少去别人家里作客,更情愿呆在屋子里。只是每逢节日,生日,周年纪念日,却老往领导家里送礼。人与人之间的交流,少了一种直面人心的坦荡。生活在城市里的人,朝九晚五,上下奔波,不过是为了得到一个几十平米稳当的容身之所。看起来,我们拥有房子,车子,票子,而实质上,大部分的人都是用金钱不断兑换物质,用以满足的内心的虚荣心,用物质来抵抗无底洞的孤独和空虚。但欲望从来是得陇望蜀,没有尽头。一方面人的精神陷入越来越空瘪的状态,寻找不到力量支撑。而另一方面,对物质的欲望越来越大,越发不可收拾。人因此成了金钱的奴隶,工作的机器。我们忘记了千百年前,曾有过的美好生活。陶渊明里“开轩面场圃,把酒话桑麻”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不是桃花园里才有的生活写照。这种意境不是环境所营造的,而是人。在一切的因素中,只有人才是至关重要的决定因素。有一片良田美玉,不是自然的造化,而是人们的辛劳成果。而桃花源,并不在远,而在于每个人的内心。
在这里,在背崩乡,我找到了失落的桃花源。这里的人沿江而居,欹枕江边,诗意的栖居。这种诗意,并不是小资的洋楼,红酒,诗歌。而是一种原始生活的质朴状态。雅鲁藏布江洗涤每个人内心的污秽,使我无时无刻不在注意自己的行为,以免显得格格不入。雅鲁藏布江承载着一个民族百年来所有的苦难与幸福,但无论如何,江河还是一样的流淌,而这里的人还是一样劳作,生活。